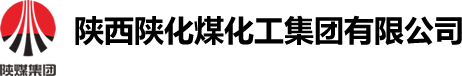没想到一次不经意间的玩笑了却我一桩心事。
停运20多年的华县火车站9月份开始恢复运营,消息传出来,我默默地在心里给自己许下了一个愿:我要坐头趟车!
我和华县火车站的不解之缘可以追溯到童年,只要出县城都是坐火车,第一次坐火车是三岁时和父亲去耀县姑姑家。小时候的眼里,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光亮铁轨就是通往外面世界的路。
离火车站几百米的原陕西省出口食品厂,是我小学时期暑假最喜欢去的地方,那里有我的三个表兄弟,更有我百看不厌的火车,那时的铁路还是开放的,我们在铁路边一玩就是一天,在铁轨上压过铁钉和硬币,也玩到忘乎所以,差点被疾驰的火车定格人生——“享年9岁”,总之华县车站给我留下了许多回忆和欢乐。
真正让我和火车站结下深厚感情的是86年,至亲至爱的爷爷应邀写下“华县站”三个字后两个月后因病去世,从此站南路成了我最爱走的路,每次从那里经过,就好像爷爷站在那里看着我。华县站停运后,我再也没有坐过绿皮车,再也听不到那个记忆中的“咣、咣、咣”的接轨声。
年初传出恢复客运的消息后,华县站三个字的去留一度成了关注的热点,但直到通车仍然沿用华县站名,具体原因不详,但却给了我莫大的心理安慰,所以听到消息后第一个念头就是:我要坐头趟绿皮车,替爷爷看看现在的盛世繁华。

国庆节过后,华县站增加了车次,有天晚上在朋友店里闲聊,朋友说第二天下午让我给他帮忙看店,他要带孩子坐火车,我不习惯守店的那份寂寞,便随口一说:“那宁愿我带孩子去坐火车。”
就这样一句玩笑话促成了我和绿皮火车之约,当即在网上购买车票,规划的目的地,本来我想去宝鸡吃凉皮,但是没有合适的车次,只有去潼关吃肉夹馍了,绿皮火车,我来了。
第二天如约成行,顺利经过安检进入大厅,候车室是在原基础上改造的,和多年前没有多大变化,增加了售票柜台和一些人性化设施,直接身份证验证刷脸进站。
绿皮车还是保持着当年的“老习惯”,晚点二十多分钟才进入站台。我如同在等待恋人般看着慢慢停靠的火车,因为是东去潼关,等车的没几个人,其中有一对母女也是和我同样目的,四岁的孩子很听话,天真无邪如同小时候的我,蹦蹦跳跳的期盼着火车停靠。想想以前坐火车是奢侈,现在却成了好奇和怀旧,感叹社会的进步。
紧接着便是进入车厢找座位。其实也不用找,环顾四周,偌大车厢没多少人,热心的列车员说:“随便坐,不用找座。”在快节奏的今天,人们出行基本上都选择动车高铁,像这种绿皮车都属于是慢生活圈的人群。
列车徐徐开出站台,两边的建筑和树木在眼帘里纷纷倒退,车厢里干净整洁,没有以前的熙熙攘攘嘈杂喧闹,地面上没有记忆中的瓜子皮,瓜皮纸屑,也没有来往的“啤酒饮料方便面,香烟瓜子火腿肠”的叫卖声,墙上车厢里到处都是提供各种服务的二维码,一切显得既亲切又陌生。

三三两两的乘客在小声地聊天,两个大姐一边吃着方便面,一边谈论着老家七块一碗的鸡汤面,我感觉她已经把方便面吃出了鸡汤面的味道。旁边座位上几个同路打工人交流着华县站开通的事情。“这车要是在柳枝(华县东边的一个小镇)能停就好了,”
“能在华县站停都烧上高香了,你想的美。”另外几人笑着回应他。孩子既好奇又兴奋看着一排排往后疾驰的树木,看着听着车厢里人群和对话,不停问这问那,我用尽了词汇才能跟得上他的节奏。
不到一个小时到站,潼关鸡鸣三省,是陕西的东大门,当年凭借天险阻挡住日本人的入侵,是三秦人民的福关,形似城楼的候车大厅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庄严大气。广场上一大群玩耍的小孩吸引了孩子的脚步,他很快的融入其中,玩的津津有味,而我成了众多老头老太中的一员,眼球不离孩子十米,买个肉夹馍都不敢进店门。在门口喊开来:“老板,夹两个馍。”
很快预定的返程时间就到了,出乎意料的是原定晚上七点的返程车晚点三个小时,只能改签七点半经过渭南站的车,打电话和朋友约好接车回华县,不得不说世事难料,上演了一个现实版的人在囧途。郁闷间,突然想起在在广场地上捡到的的一张纸,上面的一段话恰到好处的解答了我的迷惑:“快乐其实并不难,难的是你是否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,是否愿意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。”
是的,我想趁自己还未老,抓住时代进步的尾巴赶赶脚,也想重拾那魂牵梦萦的亲情,这趟车管它开往哪里,几时开几时到,这就是我想要的快乐,看来上天早有安排,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给了我合适的答案。晚上九点半,我释然的完成了约会回到家中。(维保分厂 吴颖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