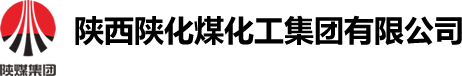周末,工作之余,补课写作业之余,我们一家人趁着三九天难得的暖阳在街道上消遣,无意间被烤蜜薯的叫卖声叫停了脚步,顺便买了一个。然而,包装袋上一句小小的广告词——“带你寻我童年的记忆”,引起了一家三口的注意。对于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而言,对于“烧烤红薯”,自然有好多久远的记忆,因此便充当一次其中的“我”,搜寻了一些由远至近的记忆来一起分享。 最早是要追溯至上幼儿班(村里没有幼儿园,就叫幼儿班)之前了,那时父亲就是村里学校的老师,加上学校就在离家不远的坡底下,虽然还没有正式上学,但也会时常背着母亲用碎方格花布制作的小书包,出现在学校的角角落落。书包里除了装一个64K的小本子和一短节铅笔之外,再就是装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大小适中的红薯,本子和铅笔自然是多余的,只有红薯才能真正派的上用场。于是在父亲的帮助下,总是迫不及待将红薯掩埋进老师们刚做完饭炉灶下的火灰里,然后既焦急又耐性的等待……烧熟之后真正享用的味道并没有深刻的记忆,只有每次漫长的等待至今令人难忘。 山里的孩子总是会想办法为自己寻找乐子的,即使是满山荒芜或白雪皑皑的冬季也不例外。这不,对小学甚至中学相当一段时期的寒假记忆就是明证。尽管冬日里暖阳难见、甚至寒风凌厉,但也挡不住孩子们寻乐的热情,吃完早饭,便三五结伴、自带工具和食材来一次“野餐”,食材就是红薯,“野餐”就烧红薯。 村庄之外,山茆沟梁之间,寻一处向阳的、背风的山湾或山脚,大家伙分头行动,“一时三刻”便备好足够的柴火,就能开烧了。具体的烧法一般有两种,一种是直接在空地上点柴生火,直到有足够的火灰后,将红薯直接掩埋进去,这种方法虽然简单,但烧出来容易“皮焦里头生”。另一种方法是在合适的地方挖一个土渠,之上用黄土疙瘩搭建一个规模适中的“堡垒”,然后在下面的土渠里点柴生火,直至黄土疙瘩烤黄烤焦之后,将红薯置于其下,倒毁“堡垒”,用火灰和烤焦的黄土疙瘩将其掩埋、烧熟,虽然程序稍显繁琐,但一般烧出来的质量可靠。其实不论哪一种方法,大家更看重的是烧烤过程,或者是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个有趣的情节或细节,真正烤出来的结果依然没有人在意。由于经常在野外点柴生火,满身满脸烟熏火燎的痕迹随处可见,稍不留心被火烧破或烤皱衣服的事情也时常会发生…… 后来,就到上中学的时候了,学生宿舍是窑洞,里面是前后两个土炕,每到冬季的时候,会在每个炕头搭起一个火炉子,然后烧炭取暖。这时,烧炭炉子底下就又为烧烤红薯提供便利的条件,由于宿舍防火灾的需要,每天上晚自习的时候都要留守一个看火的值日生,又因为不用上晚自习,还可以烧烤红薯,所以大家都非常乐意在宿舍里值日看守。那时候,无论是哪个舍友值日,除了给自己烧烤红薯之外,还要负责给其它人烧烤,一番忙碌之后,带来的是大家在就寝之前的“红薯晚宴”。 再后来就长大了、上班了,对烧烤红薯的记忆也越来越淡了,虽然在秋冬季节,街道上也常听到烤红薯叫卖声,虽然在工作之初也曾有在生产现场蒸汽法兰上烧烤红薯的经历,但很难再现当年的那种热情和心境了。 今天,也许是个意外,一个烤蜜薯,一句小广告,引发了一连串久远的记忆,也带来了一连串意外的欢欣,期间可谓忆者想忆、听者想听、吃者想吃,但愿生活中多一些有这样的意外,多一些这样的欢欣。(张向阳)